最热新闻


查看手机网站
煤海灯 —— 谨以此文,纪念母亲逝世三周年
作者 赵多献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
母亲去世快三年了,总想写点什么,却迟迟未能落笔。每当提笔,往事如煤井深处渗出的水,无声漫过心头,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。那些记忆像煤块一样黑,却也像煤块一样藏着火——那是母亲用一生点燃的光。
煤井下的灯光是微弱的,却是矿工的生命之灯。母亲的一生,便如这煤海深处的灯,在黑暗中倔强地亮着,照亮了全家,也温暖了周围的人。
母亲(1938.12.28——2022.7.9)生于广灵县蕉山乡八角地村。外祖父是在煤窑里挣扎求生的人,在日寇占领大同时期,曾被强拖至煤矿当苦工。后因劳役戕害患了疟病,他竟被残忍地抛入“万人坑”——幸而老人竟从死亡深处爬了出来,带着九死一生的气息挣扎回人间。
六岁年纪,本应是懵懂嬉戏之时,母亲却已女扮男装,随外祖父和舅父至河北蔚县煤矿谋生。小小年纪每日煮完饭送去工地,竟在这黑烟弥漫之地悄悄习得了外祖父的绝活:如何识山势,观脉络,判水情,定埋藏丰厚煤层的采掘点。
窑主初次见着这个戴毡帽的“小子”,眼里透出狐疑:“六七岁的毛孩子懂得个甚?焦窑官,莫不是戏耍我?”外祖父却笃定应道:“保你出煤,不然分文不取。”
母亲手指之处,果不其然掘出了厚煤层。那窑主惊佩之下,竟执意要将女儿许配于这位少年“英才”——待到外祖父无奈揭开“毛小子”实为女儿身的真相,一场奇缘方才作罢。
知识是沉重矿脉里透出的光,被一个瘦小的女孩悄悄擎住了。她以穿透地层的慧眼,竟在旧世界的黑暗中,为自己凿出一线光明。
母亲很爱上学,仅上了三天私塾,便被外婆叫停,虽多次哭闹,怎奈胳膊拗不过大腿。外公长年累月积攒的骆驼票(旧时地方货币)塞满了陶瓮。日本投降前夕,外婆曾劝他兑换成银元,外公却固执地不肯。最终,那些血汗钱只换来了六亩贫瘠的田地,剩下的钞票后来被用来糊了墙。
母亲十六岁那年,外公因积劳成疾去世,丧事欠下的债务如大山般压在外婆肩上。无奈之下,外婆含泪将她送到蕉山村当童养媳。在那两年里,母亲睡过柴房,咽过糠菜,却始终倔强地不肯认命。她甚至绝食三天,险些饿死自己。直到十八岁那年,她终于逃离了这个家庭,经人介绍嫁给了当时正在当兵的父亲。
父亲从军多年,参加过解放太原等多场战役,后又赴东北抗美援朝解放军后方医院。前妻独守空房数年,最终卷走全部家当嫁给了村支书。待到同母亲结婚复原回村后,又频遭村支书压制排挤,每每错失良机,幸有母亲支撑,父亲后来方在信用社寻得安身位置。
母亲将艰难日子熬成了蜜糖。奶奶染着当时可怕的“痨病”,大娘二娘避之犹恐不及,母亲却将照料之任默默承担下来。及至奶奶弥留之际,谁也不肯接纳,又是母亲令父亲把她接至家中。最终,奶奶眼含愧泪,在无声的歉意中合上了双目。母亲每每忆及,眼中亦常泛起酸楚的泪光——但我知道,那泪中沉淀着她早尝尽人间苦味的悲悯。
母亲曾有一位情同手足的闺友,也是她当家的嫂嫂。两人同食同寝,亲密到连衣物也互换着穿。岂料好友生产时遭遇难产,接生婆竟乘危坐地漫天要价,仅因两块现大洋未能凑足,好友与婴儿便双双殒命。母亲目睹惨状悲愤难忍,痛骂那黑心婆子,并立下誓言:“我必要学会接生,为乡邻分文不取!”
六十年代县里招收接生员培训,母亲毅然前往。经过180个日日夜夜的勤学苦练,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结业。她婉拒留县人民医院助产士的机会,毅然回到村里,以一己之力填补了乡村助产的空缺。其间接生上百个婴儿,父亲仇家的后辈也在其列。她分文不取,经手的孩子也从未有过意外,甚至得了“无风”的好名声。
村中与我及兄姐同辈者,大多是母亲给接的生,开的奶。尤其说起生我时,临产当日,她哄走姐姐与哥哥,阵痛间隙,母亲咬牙为自己铺好草纸,烧水剪脐——我就这样在她血汗交织的双手中降临人世。每每提到这件事,母亲的脸上总会浮起坚韧与自信的光彩。
母亲奶水充盈,我断奶甚晚。一次村里羊倌家来喊接生,母亲抱着我跑去忙碌,我竟看见她正给一个眉生间巨大胎记的婴儿喂奶。
我委屈得大哭,回家后无论她如何哄劝,我再也不肯碰一碰奶头。过年时,羊倌为感恩提来一条滴血的羊腿,母亲却坚决推辞:“别人的东西,咱不能要。” 她提起羊腿便送还回去。我内心暗恼,后来类似情形多了,竟也慢慢习惯了她石壁般的磊落笃定。长大后才理解了母亲,她推回的不仅是谢礼,更是一个干净世界的刻度
母亲的苦干与公心,被村里人看在眼中。七十年代她入党,被推为村党支部副书记、妇联主任。
为了多挣工分供我兄弟三人读书,母亲割草、浇地、赶车,男子担的活她样样都干。背草时重达一百五六十斤,她弓腰负重,步履沉沉踏在夕阳泥土路上。晚上开完会常要夜战,她竟从未停歇过,挣的工分常超过男劳力。就这样,母亲以惊人的坚韧为我们全家换回糊口之粮。
母亲多次被评为县劳模、先进工作者,出席过雁北地区劳模大会。七十年代初,一次县里推举全国劳模让她填表,她看到“是否放过羊”一栏,便摇头说:“我不合格。”——村里除放羊外,她确无活不曾干过,却就这般放弃了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机会。为了培育我们,她又屡次放弃了当“借干”的出路。
母亲识字虽少,却把没文化当做了“短病”,终生好学不辍,竭力供我们读书。哥哥1978年考上太原工学院,成为我村恢复高考后第一位大学生,母亲为此兴奋得彻夜难眠。姐姐是我们家老大,学习成绩优异,那时却靠推荐上大学,姐姐初中毕业时,村里给了个上中专的名额,作为村干部的母亲将中专名额推荐给一个更加贫困家庭的子弟,姐姐只好上了高中,毕业后加入知识青年专业队。80年顶替父亲进入农信社工作,是当时农信社的业务尖子,曾代表雁北地区参加过全省农金系统技术比武竞赛活动,名列前茅。
父亲1992年患癌离世,母亲时年五十三,独自挑起了家庭重担,为儿女奔忙。她坚韧的生命之火,仿佛永无枯竭。然而,岁月终究有其刻度。母亲八十四岁那年,夏意渐浓的7月,她心中仍牵挂着一位久病卧床、已成“植物人”的昔日老邻居。母亲瞒着我们,步行3公里独自去探望了这位老姐姐。
那份萦绕于心、无以言表的悲伤,归来后让她辗转难眠。7月11日中午,家中寂静,母亲如常劳作,却不慎摔倒。由于前一天单位组织团建,我去拍照,没有顾上去母亲家,心中莫名牵念,于十二点半左右推开了家门——只见母亲倒在地上昏迷不醒,身旁散落着拖把和一滩水渍,仿佛劳作刚进行到一半便被命运强行中断。
惊痛之下,我急唤住在附近的姐姐并呼叫医生,120急救车呼啸而至。县医院诊断为脑梗,紧急溶栓处理后转院大同市第五医院。途中,母亲还睁开眼睛看着急救车中的姐姐和我,紧紧攥着我的手,好像有好多话要说。
傍晚时分,哥哥也从太原赶往大同,此时母亲已进入ICU病房。由于疫情,我们三个不能陪在母亲身边,只能在病房外等待奇迹的出现。然而在与命运强争两昼夜后,医生最终摇头。遵从医生的劝告,我们含泪带着氧气,将母亲接回她一生守护的家中。
公元2022年农历六月十五日晚九时,那个夏夜萤飞、星斗初上的时刻,为母亲擦拭完身体,换上她多年前备好的寿衣后,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寿衣是她十年前亲手缝的,针脚细密如常。临终时,她的手指仍微微蜷曲,仿佛还攥着那把未拧干的拖把。
母亲一生如煤海深处倔强的灯,即便尘烟弥漫,也始终亮在自己认定的路上。她为新生命剪断脐带,为道义扛起冤仇,为子女让渡前程。直至生命最后,她仍心系病榻上的故人,倒下前双手还紧握着劳作的拖把。她如油尽灯枯般的燃烧自己,照亮无数人穿行尘世的风霜,温暖了我们的一生。
母亲离去,却在我们血脉里留下一颗滚烫的煤核。它无焰无烟,静静散发着温热,以坚质默然对抗着大地深处的寒冷与遗忘。这煤核般的温暖,正是孟郊诗中“寸草”永远报不尽的晖光。
那盏煤海深处的灯虽已熄灭,但母亲早已将火种埋进我们的血脉。这光温厚内敛,如春晖铺展大地,让草木枯瘠处生出永恒的嫩碧。它无声却恒定,是生命深处一泓不竭的清泉,纵使岁月流转,她的光仍在我们心中长明。
母亲虽已离去,但她的精神如璀璨星辰,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2025年7月4日
(作者单位 山西广灵农村商业银行干部)
值班总编辑 贺文生
相关推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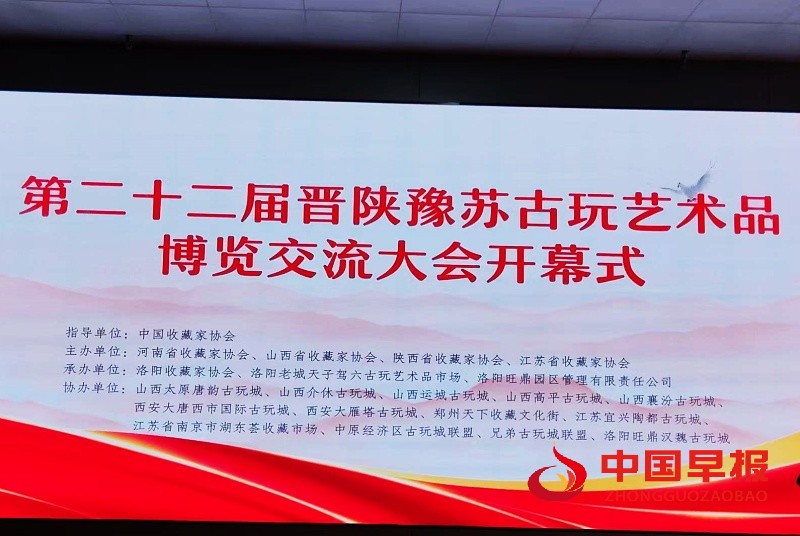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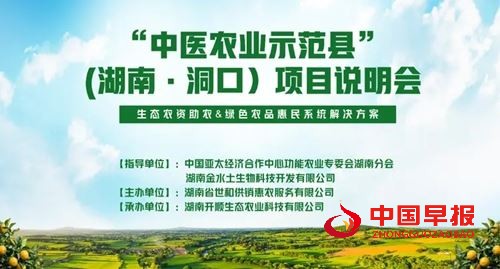




 投稿邮箱
投稿邮箱
 联系电话
联系电话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
